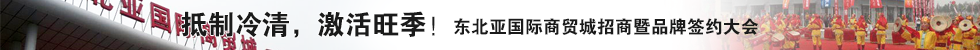从小众到大众
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中,地毯和挂毯一直与贵族、珍贵、稀有划上等号。
西方艺术家(以及建筑师)曾经深深受到地毯和壁毯的影响,同时因为他们的创造,也改变了我们对于这些物品的看法。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许多画家比如拉斐尔、夏尔·勒布伦和弗朗索瓦·布歇都曾为壁毯绘制过样板,壁毯也常常出现在许多西方绘画作品中。比如现在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佛兰德斯画派的代表人物鲁本斯就有过大量的壁毯作品。在西方开始制造地毯和壁毯之前,这些物品确实是贵族独享的珍贵进口装饰品。到了17世纪,纺织品工艺变得普及,地毯和壁毯就成为了资产阶级装饰室内环境的物品。之后,东方主义风格的流行使得地毯和壁毯的主题偏向于描绘幻想中的神秘东方,因为变成了用以刺激感官的配饰品。
直到由威廉姆·莫里斯等人发起的让艺术家参与日常生活设计,让日常物件拥有得体品质的“艺术与工艺运动”,手工艺的价值才得以扭转和重现,这种转变预示着“现代主义”的开端,标志着西方艺术新纪元的开始。
丰富内容的载体
随着手工艺技术的进步,织毯成了各种表达的载体。可以是星星月亮代表的对天文的迷惑与探索;也可以是对于不同文化的连接和包容;当然描绘动物的必不可少,人物关系也是题材之一。
现场展示的清代《花鸟纹毛毯》是中国清代时期编织的栽绒挂毯,以棉线为经纬线。此毯以红色作底,四围无边框,图案为树枝花卉纹,孔雀、飞燕、鹤、鸳鸯等鸟类休憩其间,呈现出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景象。整幅挂毯编织细密,色彩亮丽,构图协调,至为珍贵。
法德裔艺术家卡洛琳·阿珊特在伦敦生活和工作。她以即兴且不失技术性的方式运用毛料和陶瓷,并且通过梭枪上经的方法把彩色毛线固定在底层布面上。她深受德国表现主义和20世纪初原始主义的影响,青睐部落或异域风情的艺术形式,例如在突出材料的编织作品中融入面具元素。她的作品常常摇摆于民俗艺术和未来主义、现实和幻想、吸引和排斥之间。这张壁毯让人联想到一张长着胡子的脸和一只雄鹰(德国的象征),犹如一件具有巫术色彩或净化心灵的物品。她在现场展示的羊毛枪刺地毯《长胡子的老鹰》令人印象很深,这件作品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挂毯,而将毯子做成鹰的具象,毯子独有的毛茸茸的质地突出这只鹰的质感,是很有意思的创作。
地毯中与艺术家
到了20世纪,让·吕尔萨、毕加索、柯布西耶等艺术家开始重新关注织毯创作,并将其视为艺术与设计,绘画与雕塑之外的另一个方向。展览展出的几幅毕加索作品如同他的绘画一样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印记,侧脸与正面在同一平面的女人,破碎的色块,明快的颜色。织毯因其灵活性、可塑性和强烈的质感,很快成为康定斯基、索尼亚·德劳内、米罗、克利等抽象艺术家的表达语言,而后继续被用在如约翰·马·阿姆兰德、迈克·凯利等艺术家的装置作品中。
织物当然也离不开身体。织毯到了“朋克教母”薇薇安·韦斯特伍德手中,就成了华贵张扬的复古长袍,带着亚瑟王时代的繁复精致吸引观众目光。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5位服装设计师的织毯作品,它们走出了作为“毯子”的基本用途,向观众展现对于纹样、身体、材料和尺度的理解。